|
支付宝海外代充 西藏高原烈士的孩子钟建新 十八军和老西藏军人的孩子有很多,大多数很小就在西藏军区保育院,西藏军区八一校长大。小时候,不认识父母,我们印象中的父亲就是黝黑肤色,个子高大穿军装的军人。妈妈就是那个对着我们笑,伸出手抱我们的女军人。兄弟姐妹同在一个保育院,也相互不认识,这可能是保育院长大的十八军孩子们的共同经历。在保育院,八一校还有一些特殊的孩子,孩子们的父亲,有的在进军西藏时牺牲,有的在西藏平叛和对印反击战中牺牲,有的在保卫西藏,建设西藏积劳成疾的工作中牺牲,有的在往返西藏路途翻车事故中牺牲。以前保育院,八一校各个年级,基本都有这些高原烈士的孩子,这些孩子的父辈永远留在高原的烈士陵园里。这些孩子,有的岁数很小送到保育院,因岁数太小记不清父亲的面容。有些还没有出生父亲就牺牲了,没有见过父亲,没有依偎在父亲温暖怀抱里。他们看到的父亲,是照片里那个年轻军人亲切的面容。烈士孩子们对父爱的渴望,对父亲深深的想念,是我们在保育院,八一校长大,和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时光很少的孩子,也无法真正懂得、真正理解,那是烈士孩子们心里永远的痛,他们的童年,比我们少了更多的温暖。 在八一校,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姐妹,八一校老校友基本都认识的抗美援朝这对姐妹花。他们的大哥是八一校友敬重的万里大哥,大弟弟建设,小弟弟马边都是在保育院,八一校长大的。大弟弟建设和我是同一个保育院,八一校同年级的同学。在八一校时,只知建设是烈士的孩子。直到这几年,和抗美姐有联系后,才略知一点抗美姐父亲马忠先伯伯的经历。当我给抗美姐说,想写高原烈士的孩子,抗美姐找出了马忠先伯伯给战友的信,爷爷留下的资料,马忠先伯伯牺牲后,军区给抗美姐的爷爷奶奶,妈妈写的信,还有马忠先伯伯教过的学生,同是十八军老军人制作的美篇。当抗美姐给我讲述马忠先伯伯的革命经历,牺牲的情况时,数次哽咽说不下去,我留着泪记下了马忠先伯伯的一部分经历。 五兄妹的父亲马忠先伯伯,河南开封人。1939年参加地下党河南水东地委开封支部,1941年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2年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细菌学专业。抗战胜利后,豫皖苏军区六地委成立地下党开封支部任委员,分工负责河南大学地下党工作。1947年河南大学与全国各地大学一起开展反内战,反饥饿,反战争学潮,河南大学成立学生自治会,马忠先伯伯当选理事会理事,将学生运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。在指挥大学生游行时,被国民党抓捕入狱。马忠先伯伯入党时化名高峯,经党多方营救才出狱。马忠先伯伯从学生时期就参加地下党,是隐藏战线的无名英雄,为解放当时河南省会开封市功不可没。1948年研究生毕业,由吴芝圃等领导安排,从地下党隐蔽战线穿上军装,到豫院苏军区医学专科学校任教,边打仗边教学。淮海战役胜利后,豫院苏军区改编为二野五兵团18军,渡江前夕,学校更名为18军军区专科学校,马忠先伯伯任教官。渡江战役中,马忠先伯伯将生死置之度外,无数次往返战场抢救伤员。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,边行军边教学。入川后,18军奉命进军西藏,马忠先伯伯跟随部队入藏途中,接到命令,组建西南军区军医学校的任务,马忠先伯伯在组建期间,担任教导处主任和教官,为18军培养大批医务人员,分布在各医疗战线上,为解放西藏,建设西藏做出很大贡献。组建期间又接到命令,到苏联留学,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院报到,报到后才知,是苏联专家领导并担任教学的高级专业师资研修班,专业性很强。军事科学院高级专业师资研修班毕业后,晋升博士,是我军培养的第一批三防军事医学人才,毕业后的医学军事人员,全部留在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。 十八军首长张国华军长,谭冠三政委到北京开会时,向中央要求急需的医务人才,周恩来总理推荐马忠先伯伯。马忠先伯伯毫不犹豫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,和当时已调成都军区的妻子张玉梅阿姨,随谭冠三政委,李光明阿姨一起乘车回到西藏,回到老部队,任西藏军区第一任卫生防疫检验所博士所长,填补了西藏军区卫生防疫工作空白。1956年3月初,藏北地区(黑河)发生鼠疫,牛羊马畜生大批死亡,牧民也有很多染疫死亡,藏族同胞的生命和财产都受到威胁,西藏军区立即成立工作组前往治理。马忠先伯伯受令带着卫生防疫所专业人员赶往黑河后,立即夜以继日开展工作,丝毫不顾个人安危。黑河海拔高,气候环境恶劣。任务即将完成时,在安多海拔最高处,由于劳累,患上感冒,很快转为肺水肿,于1956年3月6日,牺牲在黑河(那曲)工作岗位上,牺牲时年仅32岁。 五兄妹的母亲张玉梅阿姨,河南开封人,在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读书。1948年开封解放,弃笔从军,参军到二野五兵团十八军。是背着不满周岁的儿子马万里,和马忠先伯伯一起参加渡江战役,解放大西南战役,跟随十八军走到四川,和马忠先伯伯同一个单位担任秘书工作,后调成都军区工作。跟随马忠先伯伯回到西藏后,在西藏军区后勤任秘书。马忠先伯伯牺牲后一年,张玉梅阿姨转业在西藏拉萨工作,多次调动工作,曾在日喀则,山南等地工作,在藏工作20余年,1975年内调回成都。 马忠先伯伯牺牲时,万里大哥刚在西藏军区八一校上一年级。抗美援朝双胞胎姐妹还不到六岁,和大弟弟建设都在保育院,小弟弟半年多后在拉萨出生。不到七个月,张阿姨把马边小弟弟送到成都的西藏军区保育院,自己返回西藏工作。五兄妹就一直在保育院,八一校这个家里长大。每当寒暑假到来,同学们的军人父亲刚好回成都休假,或者妈妈在成都工作,或爷爷奶奶在成都,就可以接回家度寒暑假,热闹的校园一下冷清了,只有很少部分同学留在学校,五兄妹就是每个寒暑假留校的同学。马忠先伯伯牺牲后,张玉梅阿姨一个人在西藏工作,三四年才能回成都休假。休假时只能住招待所,马边小弟弟在保育院太小,只有把四个大点的孩子接出来,吃顿好吃的饭,招待所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,搭上地铺,能围绕在妈妈身边就是一个温馨的家。张玉梅阿姨每次休假来去匆匆,看看五兄妹,还要赶回河南开封,看望五兄妹的爷爷奶奶,姥爷姥姥,休假在成都的时间短暂,无法给五兄妹一个家,无法给孩子们更多的母爱。家是什么?这是五兄妹儿时没有的记忆。万里大哥,抗美姐,援朝姐,建设,八一校毕业考上中学,中学的集体宿舍就是兄妹的家。文化大革命开始,学校停课,中学的宿舍没有同学住校,万里大哥和建设都在成都九中读书,就把抗美姐、援朝姐,马边弟弟接到九中男生宿舍住下,五兄妹终于在一起团聚,男生宿舍就是五兄妹临时的家。在这个临时的家里,万里大哥担负起“家长”的责任,学校开伙时五兄妹就在学校打饭吃,学校食堂不开伙后,万里大哥买来煤油炉子,带着弟弟妹妹学包抄手、饺子,煮面吃。春节到了,妈妈远在西藏工作,万里大哥带着弟弟妹妹,用当时凭票的定量,购买食品,糖果,又一起包出形态不一样的饺子,这个年三十,是五兄妹在一起吃的最香的年夜饭。万里大哥带着弟弟妹妹做小游戏,把纸写上数字折好,用抓阄的方法,兄弟姐妹一起抢糖吃,分糖吃,嬉戏打闹。这是抗美姐在父亲牺牲,母亲远在西藏,五兄妹在临时家里过的第一个最快乐的春节,也是抗美姐第一次对温馨家的难忘记忆。从马忠先伯伯牺牲,到兄弟姐妹们报名参军,整14年的时间,五兄妹就这样在保育院,八一校,成都的中学长大。 1969年,万里大哥,抗美姐,援朝姐,建设同时报名参军,马边小弟弟还小,继续上学。经过3个月的新兵训练,万里大哥分到昌都军分区汽车修理连,抗美姐分到林芝陆军第一一五医院,援朝姐分到林芝军分区,建设分到山西总参测绘局。兄妹三人随运送新兵的卡车,子承父业,开往西藏。七十年代,无论新兵进藏,老兵退役离藏,都只能坐卡车。卡车虽有篷布遮挡,可挡不住初春时节高原的寒风。跟随新兵连200多女兵一起进藏的抗美姐,援朝姐,一路风寒,一路颠簸,可她们心里充满热情和期待。西藏,是父亲奋斗的地方,也是父亲献出宝贵生命的地方。抗美姐,援朝姐心里共同的呼喊:爸爸,我们来了,我们离您更近了,我们会和您一样,在高原奋斗。 林芝,有西藏江南之称,气候温润,但七十年代,西藏各方面条件都比内地差,部队生活也艰苦。援朝姐身体不好,小时候在八一校,因意外导致头部受伤。马忠先伯伯牺牲后,张玉梅阿姨长年在西藏工作,意外发生后,因缺少父母的细致呵护,缺少妈妈的照顾,援朝姐头上的小包越长越大,到小学毕业时,常头痛厉害。张玉梅阿姨知道后,请假赶回来,在成都军区总医院检查时,怀疑是脑瘤,在张玉梅阿姨坚持下,川办联系去北京检查治疗。张阿姨带着援朝去北京301医院,由马忠先伯伯当年在军事医学院同时学习的同学,脑外科专家段主任亲自手术,开颅切除了已将危及生命的血块,切除一块颅骨后,右侧头上形成一块大坑,必须有支架支撑,防止与脑膜粘连。当时医学不发达,无替代支架,只能同时做开胸手术,把肋骨取下两块做头皮下的支架,开颅开胸手术连续9个多小时,昏迷4天4夜才13岁的援朝姐,在医生护士全力抢救,治疗护理下,终于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。援朝姐稍微恢复后,张阿姨把援朝姐送回学校,自己又返回西藏工作。因为这个头伤,这个大手术,援朝姐参军时颇受周折才穿上军装。坚强的援朝姐,从穿上军装到新兵连,就给抗美姐说好,对谁也不提头部受伤大手术的事,无论身体怎样,一定在部队当个好兵。分到林芝军分区宣传科电影队的援朝姐,和所有军人同样学习,训练,工作,参加生产劳动,从没提过头部受伤情况和身体情况,从没要求任何照顾。 林芝军分区派宣传队去墨脱慰问演出,援朝姐参加宣传队,随宣传队徒步去墨脱慰问。七十年代的墨脱没有公路,无法通车,一年之中有9个月不能与外界联系,被称之为高原孤岛。部队和村民进出墨脱,只能骡马驮运和肩挑背扛,路途蕴藏着太多未知的危险。进出墨脱要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隘山口,穿越阴雾不散,蚂蟥、毒虫、毒蛇出没的原始森林,随时可能遇到的雪崩、塌方、滑坡、飞石、泥石流、倾盆暴雨…。那些陡峭的山,湍急的河流,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,让徒步走进墨脱的军人要遇到无数的危险。坚毅的援朝姐,没有怕苦怕累怕危险,没有掉队,身上多次被蚂蟥咬住,只能轻轻拍打,让蚂蟥放松吸盘才能掉下来。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兵,在那样的身体状况下,跟着宣传队走过羊肠小道,穿过密林,翻过高海拔积雪山口,这需要多强的毅力。这只宣传队和亲人没有任何联系方式,徒步走进墨脱,来回用了整整28天,才返回林芝。援朝姐,是宣传队一员,胜利完成了徒步走进墨脱慰问演出任务。我无法知道援朝姐,当年徒步进出墨脱具体祥细情况,但我知道当年进出墨脱的困难和危险,知道高原烈士的孩子,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,更多的是一份坚强。 分到林芝第一一五医院的抗美姐,先是到炊事班当炊事员,当猪倌,要喂十几头肥肥的大肥猪,猪倌责任重大,因部队过年过节改善伙食,要杀猪会餐,战友们要吃上香喷喷的新鲜肉,全靠平时养的这些大肥猪。新上任的猪倌,不怕脏不怕臭,每天打扫猪圈,煮猪食,干劲十足。没想到有一天,出了一个小意外。抗美姐在给猪槽倒上猪食后,想把猪槽往里挪挪,便于大肥猪吃食,就顺手捡了块木板,用木板去推猪槽,哪知道猪槽太重,木板啪一下断了,断了的板子一下翻过来,打在抗美援朝鼻子上,顿时鲜血直流,捂着流血的鼻子,战友陪着赶紧到门诊处理。那块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油腻腻的板子,很脏,把鼻子打破,更怕得破伤风,经过门诊的处理,抗美姐鼻子被纱布包上,忍着痛又到猪圈继续工作。可鼻子上这块伤,老是不好,每天用纱布包上,后来不用纱布包时,伤还没有好,鼻子上就有时被抹上红药水,成了显眼的红鼻子,有时被抹上蓝药水,又成了显眼的蓝鼻子,让战友们又心疼又好笑。被打烂的鼻子,至今还有一块小疤痕。 在115医院,抗美姐和医院战友参加巡回医疗队,到部队为官兵做好医疗保障,到藏区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,背着小背篓上山采中药材,自制中药。夏季要上山伐木,还要挖地担水种蔬菜,储存冬季的菜。医院修房时干体力活,扛大包。当时西藏运输困难,自力更生是部队的传统,参加生产劳动,修建营房,女兵也不例外,抗美姐也是这样经受了艰苦锻炼,慢慢成长起来。从炊事员、饲养员、护理员、护士、护师,一步一步走过来。抗美姐如饥似渴的刻苦学习医疗护理技术,很快成长为医院的医疗骨干。就像马忠先伯伯那样,把精湛的医疗技术,忘我的工作态度,奉献给前来救治的高原军人们,藏族老乡,地方工作人员。 在115医院,后来成为业务骨干的抗美姐,曾多次参加医疗抢救小组的抢救治疗工作。记忆深刻的一次抢救52师154团一位战士黄兴珍,这位战士是被誉为张思德式的英雄。在部队烧炭时,这位战士晚上巡视炭窑,失足掉进炭窖里,被救时生命垂危,全身烧伤面积达85%。115医院立即成立抢救小组,全力抢救英雄战士。抢救小组医护人员,不分昼夜精心医疗,细致护理,英雄战士终于闯过休克关,感染关,慢慢恢复一些后,又对战士烧伤后痉挛的膝关节,手关节做了植皮手术,使英雄战士恢复了一部分机体功能,直到英雄战士被转送到成都的四川荣军疗养院,这段抢救,救治英雄的工作才结束。抗美姐当时是护理员,在漫长的抢救治疗中,阶段性参加了护理工作,也在陆续参与抢救小组的护理工作中,看到了英雄战士的坚强,努力学到了很多医疗护理技术。 还有一次记忆最深参加医疗抢救小组,是林芝更张林场一位职工,在伐木时被大树砸伤,昏迷不醒,因是颅脑外伤,无法搬动和汽车转运到115医院。只能就地抢救。115医院外一科主任在紧急组建科室医疗抢救小组时指出:这次派出的抢救小组,是代表115医院去抢救医治,一定要派出技术过硬,责任心最强的医护人员组成抢救小组。抗美姐被科室指令护理小组负责人,带领护理小组跟着抢救队去更张林场。到了更正林场,抢救队立即投入紧张有序的抢救工作中,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,累了就靠墙眯一会眼睛,打个盹就算休息了。林场条件差,吃住都困难,全体医护人员没有丝毫懈怠,无暇顾及休息。抗美姐负责的护理小组,细致护理,精心治疗,在更张林场艰苦环境中,抢救伤员半个多月,伤员脱离危险,伤势平稳一些后转送到115医院继续治疗,抢救小组医护人员,胜利完成了抢救任务。抗美姐也因参加这次抢救工作,带领护理小组,忘我工作完成任务,受到表彰。父亲的英雄事迹,是抗美姐前行的动力,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,做出了不平凡的奉献。 抗美姐,援朝姐都在林芝十五年军龄。抗美姐已无法记清坐过多少次车往返林芝至成都,记不清有多少次往返拉萨,山南等地。从115医院到林芝县城,林芝军分区,八一镇,林芝的山山水水,留下了抗美姐,援朝姐的身影。万里大哥在昌都军分区服役5年,抗美姐和援朝姐都在林芝十五年,兄妹三人在西藏奉献出最美的青春年华。抗美姐给我讲述部队却是很多快乐的回忆,那些艰苦的锻炼在她那如云淡风轻。抗美姐告诉我,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军人,在平凡的医护岗位上工作,没有惊人事迹,没有特殊贡献。性格开朗活泼的抗美姐,却把她的笑声,歌声,带给战友们,高原烈士的孩子,在高原经受锻炼、勤奋工作、快乐而坚强的生活。 我逐渐了解抗美姐,了解高原烈士孩子,是我在遭遇车祸重伤致残后。抗美姐和我建了微信,告诉我,她也曾遭遇车祸重伤,送川医急救时,血压几乎测不到,复合伤非常严重。在川医抢救,下病危通知书,住重症监护室,转普通病房,在川医治疗一个月后才出院,卧床半年有余。那些伤残,也曾让抗美姐一蹶不振、痛苦、心灰、消沉。抗美姐给我看了她受伤后,女儿给她写的一封信,字字是泪,句句是对妈妈的深情。在家人和亲人们的关心、照顾、鼓励中,抗美姐慢慢站起来,坚强的和伤痛博弈,忍受着巨大痛苦坚持康复。抗美姐用她亲身经历,鼓励我,给了我太多的信心和力量。 抗美姐车祸后经鉴定,胸部和双下肢都已伤残评级,每天的疼痛一直折磨着抗美姐。坚强的抗美姐,不要残疾证,带着身残的疼痛,后遗症引起生活上的诸多不便,参加了(雪域艺术团)。(雪域艺术团)是以十八军后代,西藏退役军人,以及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后代组成的业余艺术团队。多年来,为宣传十八军前辈丰功伟绩,宣传老西藏精神,自编、自创、自演了歌曲、舞蹈、歌舞剧等很多节目。抗美姐跟随(雪域艺术团),去老革命根据地演出,到学校、到社区、到农村演出,在电视台录制优秀节目。现在的抗美姐,用她惊人的毅力,已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,我们十八军后代,八一校友们,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朝气,活力四射,身残志坚的抗美姐。 我和抗美姐几年来在微信中交流,常一起笑一起哭,记忆最深的是我写出(老西藏的孩子们)那篇小文,在《雪域老兵吧》平台推出。小文里有一小节描述:我们每学期的成绩单和体检表,八一校会寄给远在西藏的父亲,父亲每个学期都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学习,生活和健康情况。小文推出的那天晚上,我和抗美姐语音聊天时,抗美姐说了一句话:“我们兄妹的成绩单,爸爸从没看过”。抗美姐和我那天晚上都哭了,我们没有更多的话语,只是隔屏不停流泪哭泣。就在那天晚上,我心很痛,第一次明白高原烈士孩子心中对父爱深切的渴望,伤痛。我们十八军的孩子,老西藏军人的孩子,从小在保育院,八一校长大,我们遗憾小时候缺少父爱母爱,缺少家的温暖,可高原烈士的孩子们,是缺失父爱,更缺少家的温暖。 在八一校,我同班同学彭瑞灵,同年级同学彭瑞新这一对兄妹,也是烈士的孩子。兄妹俩的父亲彭东源伯伯,山东平邑县人,1946年参军。随十八军渡江战役,解放大西南战役后,走到四川,十八军在乐山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后,随部队进军西藏。1954年部队安排彭东源伯伯去武汉高级步校学习,1956年武汉高级步校毕业时,已安排毕业后分配到福建的彭东源伯伯,坚决要求回到西藏,回到高原老部队。回到西藏的彭东源伯伯,1960年参加西藏平叛时,在那曲地区牺牲。父亲牺牲后,兄妹俩在八一校长大,小弟弟彭瑞汉岁数小,跟随妈妈身边长大。由于父亲牺牲时,兄妹岁数小,对父亲了解的很少,想念父亲时,只能看看父亲的照片。1969年底彭瑞新参军到50军150师48团,弟弟参军到天津警备区,妹妹彭瑞灵仍在农村当知青。到那曲烈士陵园去祭拜父亲,一直是三个孩子的心愿。可妹妹和弟弟,因身体原因,无法去西藏。退休后的彭瑞新终于如愿去了西藏,没想到因高反严重,却无法前去高海拔的那曲地区,无法去那曲烈士陵园祭拜父亲,只能遗憾的返回成都。彭东源伯伯从1960年牺牲就一个人永远留在那曲烈士陵园,彭伯伯早已化作西藏的雄伟雪山,永远守护着祖国的疆域。62年的漫长时光,62年的分离,每当清明,兄妹三人只能含泪遥远的祭拜父亲,父亲的面容永远留在兄妹三人心中。小时候不能和父亲相见,长大后又无法去祭拜父亲,这是彭瑞新,彭瑞灵,彭瑞汉三个烈士孩子心中永远的痛和深深的想念。 高原烈士的孩子,他们没因父亲是烈士去要求特殊照顾,也没有因缺失父爱消沉,他们更坚强,更努力。彭瑞新三兄妹就是这样,退役后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波折,是默默面对,是自强不息,是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工作,用坚强赢得了更多的尊重。 2021年,中央电视台七频道(老兵你好)节目组,专题制作了一集采访十八军子弟的节目。抗美姐和十八军孩子王边疆,王鲁华兄妹,一起讲述了十八军军人父母进军西藏的艰辛,保卫西藏、建设西藏,舍小家为国家的奉献。抗美姐在录制的节目中,深情讲述马忠先伯伯的革命经历,为保卫西藏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,英勇牺牲的事迹。我是流着泪听抗美姐的讲述,第一次知道马忠先伯伯的英雄事迹,第一次知道烈士孩子心里的痛和缺憾。今年国庆节前,抗美姐在《八一校友军旅岁月》网站上发出了她第一次写出的(不一样的家)。在《雪域军魂》,发出了(我的家)一文,读着抗美姐深情写出的父亲马忠先伯伯牺牲后,兄弟姐妹五个在保育院,八一校是怎样生活,那不同时期的家,烈士孩子们那些曾经的无助。我才真正了解西藏高原烈士的孩子,了解烈士孩子对缺失的父爱,渴望温暖家那种深切的痛,高原烈士孩子比我们多了更多的委屈和不易。看着抗美姐兄弟姐妹五个和妈妈的合影,看着彭瑞新兄妹三个和妈妈的合影,孩子们都那么小,合影却都缺少了军人父亲,烈士的孩子们,没有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照片。我注视着两张照片,心痛无比,眼泪不住流淌…。高原上还有和张玉梅阿姨一样的很多烈属阿姨,她们承受了太多。马忠先伯伯牺牲时,四个孩子那么小,最小的孩子还没出生,这样的打击实在太沉重,太痛苦,可张玉梅阿姨忍受悲痛,担起家的重担,在西藏坚持工作,默默陪伴烈士陵园里的马忠先伯伯。我们烈士前辈的烈属阿姨,都是那么的坚强,为祖国边疆奉献着一切。读着抗美姐写的家,我读之流泪,读之心痛,读之感动。 这篇小文,断断续续写了近两个月,在和抗美姐多次交流中,我们俩常常是流着泪交流,有时我们同样哽咽的说不下去。我们十八军前辈,我们高原牺牲的烈士,我们的西藏军人,是用实际行动,用生命注释对党的忠诚,为了保卫祖国边疆,为了建设西藏,义无反顾抛家离子,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,英勇战斗着,忘我工作着,将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西藏高原上,为我们的老前辈深深感动!西藏高原烈士的孩子们,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,无愧烈士前辈,他们是高原上的红色传承人,更多的是坚强与荣耀。我们的父辈为解放西藏,保卫西藏,建设西藏,做出巨大贡献,可歌可泣,永垂史册。致敬十八军前辈!致敬永远护卫着西藏的高原英烈! (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) 作者简介: 钟建新:1969年12月拉萨入伍,曾在扎木大站,西藏军区第四野战医院服役。退役后,考入四川行政财贸管理干部学院财会专业学习,从事财会工作,一直居住在成都。 作者:钟建新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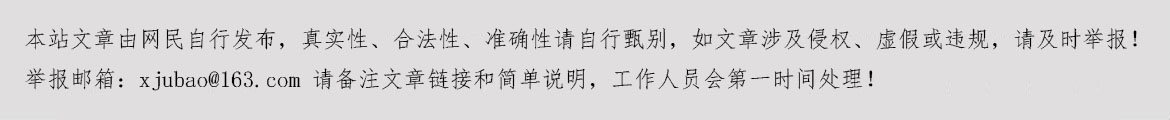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分享
邀请